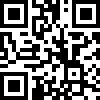冷战结束快三十年了。在许多人看来,那段历史就是美国与其主要战略对手苏联之间一场凶险的全面对抗进程。不过,美国战略界对此却颇有些不同的理解,对冷战中战略稳定关系,其视角也是多重的。
总的说来,美国的战略稳定观谈不上稳定。从“NSC162/2号文件”对战略稳定的预期设想,到“第一次打击稳定”、“危机稳定”、“军备竞赛稳定”,再到最后里根对战略稳定的颠覆,美国的战略稳定观伴随冷战对抗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出现调整。
但是,冷战强硬派信奉的技术优越和力量优势一直是其政策思想上的主线。
核对抗一开始,如何消除托马斯·谢林所说的“彼此恐惧核突袭”困境,就成为当务之急。“NSC162/2号文件”给出了一个颇具战略意境的设想,即通过核报复力建设和实现核充足,最终形成双方都不愿意发动核大战的核僵局,其中暗含了达致摆脱核困境、实现战略稳定的某种形式的双方意愿确认。
然而在冷战很长的时间里,美国人却不愿意进行这种双边关系的探讨,而是将其转化成另外一个问题,即面对核突袭恐惧,如何确保美国核报复力量安全?这就把双边关系的政治问题转化成美国力量建设和技术发展的单边性问题,是典型的工具理性主义的思维模式。
工具理性主义的一般政策路径,是对国家安全进行量化的分析,强调风险评估、成本与收益核算,遵循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思维模式,从“最坏假设”出发制订安全战略,追求自身实力的最大化优势。
在工具理性主义的指导下,美苏战略稳定从一个双边关系的问题变成了美国如何单方面取得“第一次打击稳定”的问题,即如何确保美国核报复力量的安全有效,迫使苏联不发动核袭击。以“北极星”潜艇为代表的机动性和隐蔽性能优越的战略技术突破,是美国实现战略安全保证的关键。说白了,美国追求的不是真正的稳定,而是以力量和技术优越为内涵的战略优势。
艾森豪威尔在离任时曾告诫说,要警惕来自军工复合体的威胁,警惕美国的公共政策被科学技术精英所绑架。但事实正是如此,艾森豪威尔自己的政策也强化了这一事实——除了大力发展洲际弹道导弹,他还积极推进反导导弹系统的研究,1958年的“防卫者”项目是之后“卫兵”反导系统乃至里根战略防御计划的基础。
美国不少战略家都指出,过分依赖技术和力量的战略路径难以应对现实世界的复杂局面,也难以真正有利于美国的长远利益。例如戴尔·沃尔顿和科林·格雷就曾分析道:即使大国或大国联盟之间在军事力量上相互匹敌,国际体系仍然可能是深度不稳定的状态,过分关注武器常常会导致对更关键因素的忽视。是否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由导弹或潜艇的发射重量来决定的,而更多是由于领导人的个性、价值观,政府是否决策谨慎、合理的战略判断,以及机遇来决定的,军事力量只是构成国家整体实力的许多因素中的一个。
基辛格同样认为,政治稳定和国际体系稳定高于单纯的军事战略稳定。在面对强硬派制造的军控谈判困境时,他曾质问道:“看在上帝的份上,到底什么是战略优势? 这些数字层面上的问题有什么政治、军事或实际的意义吗? 你能用它来干什么?”
但即便是基辛格,也无力改变些什么。在1970年代美国的对外政策中,他扮演的不过是一个过渡者的角色,其作用在于化解美国处于相对弱势时所面临的相对困境,一旦国家力量出现转机,强硬政策必然成为美国的选择。
美国追求技术和力量优势的战略观与两极对抗的基本战略结构相互强化,决定了真正的政治稳定和战略稳定是无法实现的。无法摆脱安全困境的美苏始终无法相信对方,也总是有意无意地夸大对方的军事力量与战略意图,指责对方破坏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共识。
这种战略互疑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总是出现基于“最坏假设”的战略猜疑和不断升级的敌意。一种有意的限制性行动,本意是要达到缓和关系的结果,却往往被对手理解为另一种全力挑战的前奏,而非战略克制。
由于缺乏有效的相互了解和沟通的机制,美苏双方也确实常高估对方的武器性能。在20 世纪80年代初,苏联认为,美国洲际弹道导弹的更高精确性,与其他因素一起,使美国核武库的有效力量增加了3倍。美国也严重高估苏联在20世纪的70年代末80 年代初洲际弹道导弹的精确性。事实上,到1991 年解体时,苏联还没有达到美国情报机构估计的它在十年前就已经达到的军事打击水平。此外,美国官员往往有意在公开场合夸大“苏联威胁”,以获得对扩张军力的政治支持。
随着战略竞争的推进,双方核武库不断扩张,战略技术也不断翻新,对抗在猜疑中日益尖锐,真正的战略稳定遂无从谈起。根据托马斯·谢林的理论,即便是敌对国家之间,也总有共同的军事利益,这是军备控制的基本前提假设。对于这一点,美国国内一直没有共识,在政治层面上对双边关系共同利益的探讨也备受局限。
而工具理性主义要求美国对自身和对手的实力不断进行重新评估和认知,这个动态过程决定了美国政策的动态性。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强硬派的路线很容易得以确立,对实力地位和战略优势的追逐反而构成了政策动态性中不变的诉求。
在与盟友关系方面,政策动态性变化的一个重要使命是维系美国对西方阵营的领导力。这种领导力要求美国保持强大的核武库与战略投掷力,以确保美国威慑延伸的可信度。就这一点而言,战略层面的完全稳定与美国的领导权之间存在着内生的紧张关系,因为它会导致盟友对美国核保护伞倚重的减弱
由于在进攻性战略力量与战略投掷力上拥有相对优势,美国的相关决策并不追求取消核对抗与核威慑,而是希望通过占有优势的核对抗与核威慑最大限度地达到美国需要的战略效果。在最基本的目标(即消除核冲突的恐惧)在技术和力量上实现后,美苏战略稳定关系的重要性即被超越,它随后成为美国维系主导地位的某种调控手段。因此,美国通常倾向于在技术和力量层面与苏联讨论战略稳定问题,而拒绝从政治层面与苏联达成真正的战略稳定共识。
在更普泛的层面而言,真正的战略稳定只是一种理想形态的大国战略关系或国际战略态势,它在根本上受制于大国关系的动态性,受制于大国力量和政策的变化。
在冷战时期,美国作为拥有战略优势一方所秉持的战略稳定理念及其进行的对外政策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冷战的进程。就美国而言,冷战时期的战略稳定观可以理解为:通过确保以核报复威慑力量为关键内涵的战略力量和技术优势,以及通过主导与苏联的力量较量和战略博弈进程,从而达到对国际战略态势的主导性塑造。
在美国战略界看来,冷战并不仅仅是美国与苏联之间、北约与华约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紧张对峙,它还是美国作为主导国家,经由一场非武力的持续运作与博弈,而最终在与主要对手的较量中取得胜利的战略关系进程。如今,冷战的概念在美国国内屡屡被提及,并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历史来源,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解。这或许也能很好地解释为何美国相当一部分的政策和战略研究者对冷战这一凶险的国际政治现象,表现出一种并不反对的态度。
-----
本文节选自作者刊于《当代美国评论》(2018年第3期)的论文《美国战略稳定观:基于冷战进程的诠释》。为阅读方便,略去注释。作者葛腾飞系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澎湃”经授权选编。